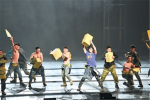電視劇《三叉戟2》收穫好評 原著作者兼編劇接受採訪
原標題:電視劇《三叉戟2》收穫好評 原著作者兼編劇接受採訪(引題)
呂錚 技術爲繮 讓靈魂這輛馬車跑得更遠(主題)
北京青年報記者 張嘉
作爲《三叉戟》原著小說作者及同名劇集編劇,呂錚注意到一個有趣現象,在《三叉戟2》熱播期間,很多觀衆在重溫《三叉戟1》,時常看到“二刷”“三刷”的彈幕,那些交織在案件中的忠誠信仰與市井溫情,總能引發觀衆反覆琢磨的興致。
《三叉戟2》以煙火氣包裹反詐內核,以幽默消解沉重,讓觀衆在笑聲中記住防騙法,成就了動人的反詐課——它並不塑造刀槍不入的英雄,而是講述一羣會疲憊、會較勁、會爲生活瑣事皺眉的普通人。
這份真實感,或許源於呂錚的雙重人生軌跡。他在經偵系統紮根二十餘年,而作爲作家,他堅持用業餘時間寫下了21部小說,將警隊裡那些鮮爲人知的無奈與堅守,揉進字裡行間。
近日,呂錚在接受北京青年報記者專訪時,談及創作初心,他坦言,正是對警察職業的深切熱愛,驅使他持續書寫正義戰勝邪惡的故事,“這份工作越久,越能觸摸到社會的真與光”。
至於大家關心的《三叉戟3》,呂錚笑說目前尚無計劃,他透露正在創作一部名爲《雙刃劍》的劇集,“肯定會是《三叉戟》的升級版。我自己也非常期待。”
越是小案件,越難創作
記者:《三叉戟1》於2020年播出,而《三叉戟2》在今年與觀衆見面,時隔五年。請問《三叉戟2》是什麼時候啓動的呢?
呂錚:《三叉戟2》早在2021年就啓動籌備,我們希望《三叉戟》是一部貼近百姓、真實接地氣的警察生活劇,不靠驚險獵奇,不靠血腥暴力。第一部聚焦P2P和非法集資等犯罪,第二部選取傳銷、養老詐騙、網紅美容貸、AI電信詐騙等題材,都貼近百姓生活,希望讓觀衆在觀劇的同時也能受益。
記者:《三叉戟2》被稱讚爲非常好的“反詐宣傳片”,這是不是在創作開始時就有意爲之?
呂錚:是的。國家反詐宣傳力度很大,我們也在思考能否通過《三叉戟》,把反詐知識深入人心,讓觀衆有所觸動、有所收穫?我們希望《三叉戟》系列不僅好看,還能多一份社會意義——清晰展現騙子的套路,讓觀衆看清騙術、提高警惕。老實說,《三叉戟》創作很難,它聚焦小案件,而非驚天動地的大案。但只要能讓觀衆多一分警覺,哪怕只是微小的觸動,也是善莫大焉。
記者:《三叉戟2》中從“大背頭”“大棍子”和“大噴子”這“老三位”去旅遊時發現了傳銷,又從體檢免費送雞蛋,延伸到了“以房養老”的騙局,這些案件層層勾連環環相扣,請問您是如何設計這些情節的?
呂錚:案件層層勾連,是我們創作的重點。有位老師曾說“用一根針挖一口井”。《三叉戟1》的案件按樹狀結構展開,每破一個小案就像拼起一塊拼圖,多塊拼圖形成一個高潮。高潮過後,又陷入困境,再掀起幾個高潮,最終匯聚成大結局。《三叉戟2》也沿用了這種形式。籌備初期,我先梳理案例,確定基調,然後以這些案件爲主線展開創作。
記者:《三叉戟2》延續了第一部的原班人馬,呈現出原汁原味的精彩演繹。尤其是陳建斌、董勇和郝平,他們將“三叉戟”詮釋得栩栩如生。把他們湊在一起容易嗎?他們在拍攝時有沒有什麼即興發揮?
呂錚:《三叉戟1》雖非熱門題材,播出熱度卻很高,三位主演——建斌老師、董勇老師、郝平老師也收穫了良好反饋。因此,提議拍攝《三叉戟2》時,他們一致叫好。拍攝現場,三位老師有很多即興表演,劇中不少喜劇效果都來自他們的現場發揮或對劇本的靈活演繹,效果出奇的好。每次去現場,我總能發現新的驚喜。
從無到有好做從1變成1.5很難
記者:相比於第一部,《三叉戟2》編劇的難度和挑戰在哪裡?
呂錚:其實,《三叉戟1》好寫,因爲它是從0到1的開創。觀衆此前很少在影視作品中見過這樣的警察形象,親民又溫和,每個人物都有自己的困境和前史。但是從1變成2,甚至只是變成1.5,就很難。“大棍子”和“大噴子”的故事在第一部已落下帷幕,三人之間的那種微妙抗衡也不復存在。於是,《三叉戟2》只能另闢蹊徑,通過人物關係的錯位,讓角色之間重新“活”起來。
“大背頭”崔鐵軍是“三叉戟”的靈魂人物,我們在第二部中讓他有了更年期綜合徵,有了中年危機;還增加了“大棍子”徐國柱和徐蔓之間的情誼;“大噴子”潘江海也有新的故事線,他一心想要升官,卻仍未能如願……這些細節讓角色更加立體,也讓劇情不再枯燥。
《三叉戟2》播放的時候,排在劇集排行的第二名、第三名,而《三叉戟1》也跟着衝到了第六名。這說明很多觀衆在看完《三叉戟2》後,又回去重溫第一部,這讓我覺得特別有趣。
記者:“三叉戟”各有鮮明性格和成長軌跡。您在塑造他們時,是否有現實原型?
呂錚:這三個人物肯定有原型,但創作時我不會依賴單一原型,而是從“量”與“質”的關係入手。接觸足夠多的人,自然會提煉出“典型人物”或“立體人物”。不能把人物寫成平面化的“工具人”或“紙片人”。比如這三個人分別來自經偵、刑偵和預審,經偵會查賬,刑偵會抓人,預審會審訊。如果只突出他們的功能性,而忽視他們的前史和人物關係,那角色就會顯得單薄。
在創作《三叉戟》小說之前,我花了幾年時間去打磨這三個人物。爲什麼要給他們起外號?就是要打破他們“高高在上”的工具人形象,把他們拉到塵埃裡,賦予他們缺點。每個人物出場時都在谷底,這樣他們纔有上升的空間,纔有故事可講,才具備複雜性,也才能引發觀衆和讀者的共情。寫三個老警察也是很有挑戰的,因爲它是反市場的,不是熱點,沒有“流量”,所以大家喜歡《三叉戟2》,我非常欣慰。
記者:陳建斌、董勇和郝平將這“老三位”塑造得太經典了,以至於觀衆都在催更《三叉戟3》。
呂錚:目前,《三叉戟3》還沒有計劃。觀衆認可《三叉戟2》,歸根結底還是因爲人物有勁道。我相信,好的文藝作品一定是人物立體、人物關係牢固,以人帶事。其實,開篇就是爆炸、兇殺、碎屍,這些好寫,而我努力做的是把小案件寫得精彩,用人物關係之間的變化,來推動小案件的發展。運用抽絲剝繭的小案,讓觀衆看到這三個主人公怎麼在案件中各施所長,共同發力。
我覺得這可能是《三叉戟2》的一個特色,我們深入生活,從真實中汲取靈感。《三叉戟2》裡面的很多笑料,包括真假崔鐵軍的橋段、將“劇本殺”融入破案的情節,以及結局的爽感,這些都是在真實基礎上的藝術昇華。
《三叉戟2》沒有爛尾,這離不開成功的人物塑造。“三叉戟”並非傳統意義上的英雄,他們只是普通人。奔跑時,他們會氣喘吁吁;面對困境,他們也會被誤導。正是這種非典型英雄的塑造,讓觀衆更容易在人物身上找到共鳴,進而接受他們,認同他們的價值觀。
吸取第一部教訓設計一個讓人喜歡的女孩
記者:《三叉戟2》中徐蔓這個角色非常招人喜歡,在一部男人戲裡,她非常搶眼,請問您是怎麼創作的這個人物?
呂錚:《三叉戟1》中,師徒四人形成了一個完整的閉環。到了《三叉戟2》,徒弟小呂該如何延續成長?第一部的女性角色不夠討喜,我們從中吸取了教訓。於是,在第二部裡,我們設計了一個討人喜歡的女孩,她和小呂截然不同。小呂內斂靦腆,是個技術理工男;而她能文能武,很颯,行動力強,是小呂的“反面”。
對於“老三位”來說,徐蔓與他們的人物關係也很有意思。徐蔓是從省廳空降的“光環少女”,她的設定也與“老三位”處處相反:破金盃對應好摩托,年長對應年輕,男性對應女性……形成鮮明反襯。作爲“三叉戟”的二徒弟,她一登場就充滿個性,與“老三位”展開博弈。
從表面看,觀衆喜歡徐蔓是因爲演員演得好,故事寫得精彩。但從劇作理論和技術層面看,徐蔓之所以吸引人,是因爲她爲劇情注入了對抗性。第一部裡,董虎之所以受觀衆喜愛,正是因爲他與“老三位”針鋒相對,又有血有肉。第二部中的徐蔓也是如此。所以,萬變不離其宗,回到根本就是塑造好人物。
記者:未來是否會考慮以女性爲主角的衍生故事?
呂錚:我正在創作一部衍生作品,但並非是《三叉戟》的故事延續。小說開篇分爲四段,前三段用第一人稱講述三個輕科幻故事,相互交織;到第四段,以第三人稱整合線索,形成閉環,推翻前設,製造雙重高潮。這種結構極具挑戰性,其中一個核心單元是從女警察視角展開的。
創作中的“貼地飛行”和“天馬行空”
記者:因爲您多年來從事經偵工作,請問故事中的真實案例和藝術加工,您是怎麼平衡兩者的?
呂錚:很多人覺得我從事公安工作,寫公安題材是“近水樓臺先得月”。其實,掌握多少案件並不重要,因爲很多素材大家都能從網上找到。但當過警察,就會有一種獨特的現場感——你是事件的主導者,這種身臨其境的感覺是採訪換不來的,也是我的獨特優勢。然而,這個職業也會束縛你,讓你不自覺地給自己套上某種限制。
所以,我在創作中要求自己把握住兩個度,第一個是“貼地飛行”,創作絕不能偷懶。比如,不能只靠閉門造車,躲在書齋裡憑空編故事,這樣雖然省力又快,但一旦養成偷懶的習慣,寫一兩個或許還能投機取巧,但寫到三五個,作品質量就會斷崖式下滑。
第二個就是要敢於“天馬行空”。創作時,要用旁觀者的眼光去看待、審視自己和故事。一位老警察曾說過:“要當好警察,別輕易信自己,也別輕易信別人,只信證據。” 就是說你不能過於相信自己,當警察如此,搞創作同樣,唯一要相信的是傾聽自己的內心,所有的東西都從生活中撈出來。
記者:《三叉戟》系列中三位中年警察的設定引發了觀衆廣泛共鳴。您在創作時是否也想通過他們,探討年齡焦慮、職場邊緣化等社會議題?
呂錚:不只是中年危機,現在還有“30歲現象”(30歲左右的職場人面臨諸多挑戰和困境)。其實,很多危機都源於內心,曾國藩說過,“物來順應,未來不迎,當時不雜,既過不戀”,我覺得很有道理。守在書齋裡、辦公桌旁焦慮是沒用的,你要主動下場。在文學創作時,要在寫作過程中發現問題,一遍遍修改、修正。這可能也是這兩年我創作的一個變化,就是我要用靈感作爲馬車,用技術作爲繮繩,駕馭靈魂,讓這輛馬車跑得更遠。
《三叉戟》就是一盤“家常菜”
記者:《三叉戟2》中,大家除了愛看破案,也愛看“老三位”的互動,您如何平衡“現實主義底色”與“戲劇化娛樂性”之間的比例?
呂錚:沒有什麼比例,我們這劇的定位就是輕喜劇,閤家歡。《三叉戟》就是一盤家常菜,就像我出差很久回到家,愛人端上一碗熱湯麪,既養胃又舒服。我很喜歡《父母愛情》,它講述普通人的悲歡離合,展現人生百態,我設想的《三叉戟》也是如此:三個穿着警服的普通人,在辦案中看盡世間百態,再從外部世界反觀自身。
《三叉戟2》中所有故事都是從現實中生髮,也就是現實主義底色,至於娛樂性,我們寫的畢竟是一個戲,它高於生活,要給觀衆帶來快樂。現在的反饋也讓我們欣喜,所有我們當時設計的點,觀衆都覺得挺有意思,包括結尾的兩集。說實話,最讓我忐忑的就是結尾。這兩集的劇本是在拍攝過半時重新打磨的,因爲感覺原來的劇本傳統了些,想着能不能徹底顛覆一下,於是我就利用週末去了拍攝地,連續聊了一天多,把框架聊出來了。這個新框架的結尾就是讓觀衆解恨,讓警察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懲治壞人。當時弄完以後,我擔心有點“飛”了,但沒想到觀衆看完以後覺得很嗨。
記者:身兼作家和編劇,您認爲小說和劇本最大的創作差異是什麼?做多了編劇後,對您寫小說有什麼幫助嗎?
呂錚:劇本跟小說的差異很大,雖然同屬於文學,但小說更注重心理描寫,也更個人化。編劇就複雜多了,一部劇可能有上億播放量,所以得儘量滿足大部分觀衆的審美,要取中,但這並不是要把個性拉平,而是從共性中找不同。小說和劇本雖着力點不同,但一脈相承——人物要立住,人物關係要紮實。
編劇經歷讓我接受了很多戲劇培訓,這對寫小說幫助很大。以靈魂爲發動機,靈感爲種子,技術爲方向盤,就能更好地駕馭寫作這輛車。
希望兒子長大後不會羞於和朋友談起我的作品
記者:《三叉戟2》的技術升級了不少,劇裡表現的,就是我們現在的經偵水平了嗎?
呂錚:戲劇終究是戲劇,“真實”也是“僞真實”,劇中那些預審技術、抓捕方案甚至一些奇思妙想,其實都是爲了營造辦案的“驚險奇特”而已,不是現實的照搬。
傳統創作是從A到B、從B到C,直至Z,比如從指紋找到嫌疑人,再抓到犯人。對這種套路,觀衆不再買賬。那怎麼吸引觀衆呢?我們在偵破中故意設置誤導。比如從A到B推進到W,卻發現全錯了,再從W回到A,最後從A曲徑通幽直達Z。這種反轉和曲折,纔是觀衆愛看的,也更貼近生活本真。
記者:近年國產刑偵劇逐漸從懸疑獵奇轉向職業寫實,您如何看待這種趨勢?
呂錚:我覺得這兩類作品可以並行不悖,除了追求市場效益,希望創作者能多考慮社會影響,肩負起社會責任,這樣的作品才更有價值。我希望兒子長大後看我的作品,不會覺得羞於示人,不會對朋友說“我爸寫的都是血腥暴力,別看了”。相反,我希望他能驕傲地說:“看看我爸年輕時寫的《三叉戟》,挺有意思的,這老頭兒寫了另外仨老頭兒。”對我來說,這種認可是生活給予的饋贈,是任何東西都換不來的。
一根針挖一口井一步一個腳印往前走
記者:這麼多年來,您的創作都是利用工作之外的業餘時間,可是非常高產,請問您有何秘訣?創作的動力是什麼?
呂錚:我用21年的時間寫了20本小說,其實並不算高產。一年寫二十多萬字,參與編劇,是幾十萬字。沒有秘訣,就是用一根針挖一口井,一步一個腳印地往前走。我常和兒子說,時間不是別人給的,而是自己擠出來的。早年押送犯人從成都回來,坐三十多小時火車,我就在車上寫了一萬多字。從二十多歲到現在,我的業餘時間、節假日和週末,基本都在寫作。
平時遇到鮮活的人物,我會進行大量採訪,但並非功利地爲寫某部小說而採訪。我平時廣交朋友,大量接觸各行各業的人,從這些交流中汲取靈感,讓故事的種子生根發芽,形成作品的框架。我的創作庫裡有很多“花盆”,接觸了許多老警察後,某個“花盆”裡突然冒出一顆種子,我便慢慢打磨,最終長成《三叉戟》。我不是爲了寫某個故事而採訪,而是從採訪中發現故事,再讓它長成文藝作品。
所以,時間從來不是問題,關鍵在於你能否駕馭自己,擺脫拖延症。寫作是對一個人的巨大磨練和修煉,而我寫作的動力,就是熱愛。
記者:都說“文如其人”,一部作品很能反映寫作者的價值觀。
呂錚:是的,劇中對人物的發問,也是對創作者的自問。在《三叉戟1》裡,“大噴子”說:“我走了這麼久,突然忘了爲什麼出發。”所以第一部的主題是因夢想而重裝上陣;第二部的主題就是如何正視自己,這同樣是我作爲創作者,需要時時自省的問題。
很多人會告訴你該寫什麼,告訴你哪些題材有熱度、哪些內容短平快。但我真正的寫作目的到底是什麼呢?我要找到自己爲什麼而寫,明白自己爲什麼而活,以及怎樣才能過上有意義的生活。這不是誇誇其談,創作者必須要有堅守,作品才能與衆不同,才能不隨波逐流。
來源:北京青年報